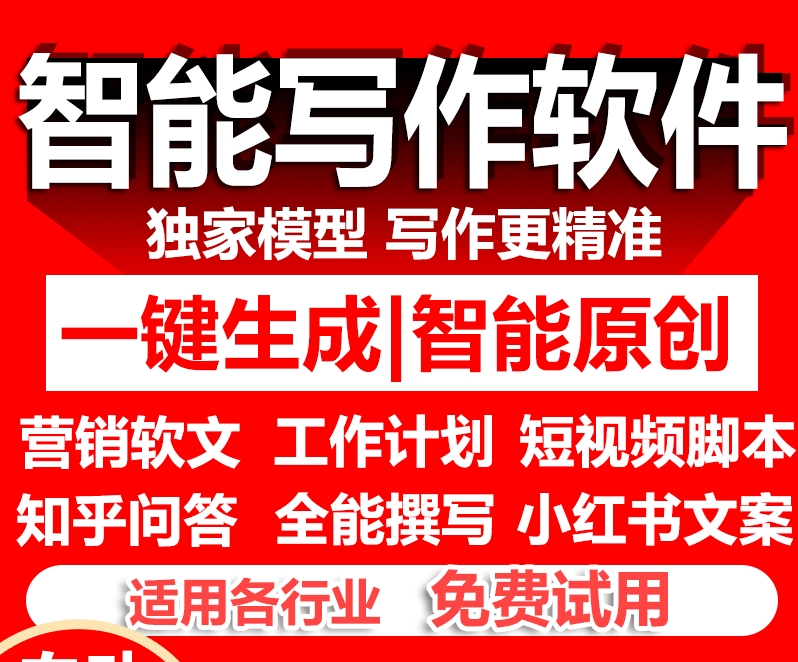共享单车暴露国民素质?应先反思“共享经济”自身
[摘要]“共享经济”与其说这是互联网公司的运作模式,不如说是推销给用户的价值观,用以号召和动员消费者自发自愿地贡献时间、精力、资源和数据为己所用的营销策略。

被破坏的共享单车。
最近朋友圈又被共享单车刷屏了:继上海大叔把摩拜扔进黄浦江之后,网友们纷纷晒出各地共享单车被拆卸破坏、被改头换面加上私锁变为己有、被强行圈地收管理费、被乱停乱放阻塞交通的照片,并表达了对国民素质的担忧,甚至有人长叹:中国人不配使用共享经济。但这些奇葩行为很多已经超出道德范畴,属于违反交通规范和社会治安管理法,是法律层面的追惩问题(侯虹斌)。也有人不同意国民素质论,立足点却是资本有力量,不需要政府和公众监管,靠公司创新就能解决(新京报)。

在这场国民素质大讨论中,不论正方还是反方,都将共享单车服务视作进步力量,却较少有人对共享经济本身存在问题的反思。从摩拜单车被人为损毁和抛掷、Airbnb住房被租客粗暴对待等等社会新闻报道中,似乎只能看到,传统行业的因循守旧和普通个体的“素质低下”,并且往往以前者的保守落后来体现“共享经济”的进步文明,但唯独欠缺对“共享经济”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如胡凌所说,“共享经济”这个概念本身已经被意识形态化了。Airbnb短租、摩拜/ofo单车、优步/滴滴打车、58快运/货拉拉等一拨以调用配置线下物质资源的互联网企业无论是在当下的新闻报道还是街谈巷议里都被视作典型的共享经济。但这里的“共享”得打上双引号:因为共享并非共同享有或者免费享受,用户/消费者是通过企业打造的互联网平台资源配置,按市场价格付费获得私人汽车、单车、住房以及其他物质资料在一段时间内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


被故意损坏的单车坐垫。
祛魅“共享经济”:自由分享话语掩盖了作为数字劳工的消费者与平台间的不平等
经济的本质是社会交换。美国法学教授劳伦斯·莱斯格指出,人类社会的两种基本经济模式是商业经济和共享经济。商业经济作为交换对象的是可见的物质形式,例如金钱、有形资产等等;分享经济则是基于社会互动的日常实践,交换的是不可见的社会价值,例如情感、人际关系、集体认同、名声等等。商业经济是资本市场的运作方式,而我们所理解的公共生活和社群共同体则是建立在共享经济的基础上:朋友之间分享书籍、电影和音乐,并不需要向对方付费;同事开顺风车捎上你,也不需要你为之买单;《星球大战》粉丝基于对电影的狂热而私下创作衍生作品,没有从中获得任何金钱报酬。这些无法被简单化约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交换,我们称之为共享经济。互联网的技术革新带来新经济模式:当线下日常生活的共享经济模式迁移到线上,例如书籍、电影、音乐的共享,则为互联网公司免费提供了生产资料用于商业经济,就连用户的个人资料和上网行为的收集、研究和利用本身也包含了巨大的商业利益。这种商业经济与共享经济之间边界的模糊和模式的混合,被称作互联网时代所造就的第三种经济形态:混合型经济(Hybrid economy)。莱斯格也只是止步于指出混合经济的巨大商业潜力,而没有对混合型经济背后的权力运作展开批判性分析。当下火热的共享经济绝非字面意义上的共享经济,实则是混合型经济。 “共享经济”与其说这是互联网公司的运作模式,不如说是推销给用户的价值观,用以号召和动员消费者自发自愿地贡献时间、精力、资源和数据为己所用的营销策略。这套具有浓厚后福特主义色彩的自由分享话语掩盖了消费者作为数字劳工与企业平台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权力不平等。
以网约车为例,早期滴滴、优步通过平台算法优化配置私家车资源、打价格战吸引消费者纷纷转向网约车服务,但当烧完风险投资可以提供给司机和乘客的补贴,滴滴又合并了优步形成行业垄断之后,价格就会随公司意志而调整提高,正如现在很多人的切身感受:滴滴打车越来越贵,还不如出租车。当遇到交通高峰期,不加价就根本打不到车,最后就是谁有能力付更多的钱谁才能打车。平台规则完全由公司制定,既没有经过政府监管,也并非司机和用户可以议价。而传统出租车行业因为有物价局的定价标准,所以提供价格相对稳定的租车服务。传统出租车公司的人工成本还包括司机的五险一金,司机需要向公司缴纳“份子钱”获得运营执照,出租车公司也与保险公司有着固定的保险理赔合同,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乘客可以直接向出租车公司理赔。而滴滴从早期以私家车车主、传统出租车司机为主的个体化运营转变为公司大量购车招募全职司机的公司化运营,不断通过灵活分散的租车服务外包绕开了这些人工成本,将过去的“黑车”纳入平台信用评价与活动积分的游戏规则。但同时却没有提供雇员与传统租车行业相同的社会保障,全职司机随时面临被解雇的风险,全职司机绝大多数为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外来流动人口。香港中文大学一项针对全国出租车司机的问卷调查报告显示,网约车服务并没有改善司机的劳动状况,反而是减少了收入(42%),加大了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57%)。因而可以说,消费者和司机都只是在刚开始可以从“共享经济”中分得短期红利,但长期以往,网约车公司的目标是击垮并取代传统出租车行业,重新洗牌和制定行业规则。全职司机的社会劳动保障制度将因为传统出租行业的衰落而面临崩塌,消费者个人也面临交通成本增加打不起车的困境和遭遇交通事故难以索赔的潜在风险。打着“共享经济”的网约车利用灵活用工和劳务外包,规避政府管制的方式最大化平台自身的商业利益。

除了劳动者的社会福利和消费者的安全保障的缺失之外,不为人注意的是,用户和司机还是公司平台的免费数字劳工。信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就是信息本身,而司机和用户使用平台产生的数据就是产品,而这些劳动被企业以优化服务的名义无偿占有、使用和营利。当下的大众媒体报道却都指向传统行业的保守落后和司机、消费者个人的“素质低下”,为新经济的长驱直入提供合理性,却无视其对劳动者权益的强制削减和对消费者数据的无偿使用,鲜有对互联网企业的数据搜集与监控、消费市场调查、广告营销公关等信息管理与控制活动的描述。对于“共享经济”的企业而言,最大的财产不是房产、汽车、自行车等物质资料,而是庞大的用户基础和生产的数据,通过调配跨区域的个人需求和物质资源来完成,而这些必须依靠用户的主动配合和使用,这些由分散个人无偿提供的时间、注意力和数字劳动被视作理所应当,而用户数据库具备重要的市场调研和营销推广价值,技术则增强了企业对市场的科学管理,通过刺激需求、记录品味和监督消费等等技术手段来作为企业市场决策的重要依据,建立更为有序和可控的市场环境,因而在用户个人看来似乎无足轻重的信息(这些信息被抹去个体痕迹而作为消费者群体特征被使用,与我们通常理解的“隐私”是不同的概念)被大规模收集之后就有着极为重要的经济价值。
而被无偿使用信息的个人往往没有拒绝企业隐私搜集的选项(opt-in/opt-out),也不具备对信息如何被监测、搜集、使用和贩卖的知情权。在大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中,人自身日趋被降低到数据的地位,成为企业监测、分析和计算的对象。信息技术升级了信息资源所有者(公司)对信息搜集和积累的能力共享经济素质共享经济素质,推动对信息更有效的集中和系统的垄断,让数据监控无所不在和无时不在,但公众却没有获得同等的监督权利和制衡筹码。其次,“共享经济”也存在对使用者的时间和空间的殖民。时间的殖民化意味着用户在工作以外的闲暇时间也在这种资本逻辑支配下变相成为一种消费“劳动”,人们使用软件打车自助式完成接单、沟通、评价与结单的行为大大节省了公司的人力资源成本。空间的殖民化则是指新技术打破传统租车行业的集中管理和准入标准,给用户带来表面上更多的选择和自由,但离散化并不意味着走向自由民主,而是优化和精简了控制权力的有效行使。如我们所见,滴滴合并优步继而采用全职雇佣司机的策略,公司运营将进一步集中化和一体化,所谓的离散化和个体化只是使用权力在普通用户和兼职司机群体中的组织形态。
当然很多人对所谓的“共享经济”有着方便、快捷、低廉的良好使用体验,并且主动认同于这些企业的品牌宣传话语,这和企业平台对用户信息与活动数据的无偿占有和利用并不矛盾,也恰恰因为前者,后者容易变得隐蔽而难以察觉,甚至因为“搜集是为了优化服务”而获得正当化。耐人寻味的是,跨国IT企业非常擅长本土化包装,例如作为营销策略推出的 “人民优步”,实质是利用平台优势调动和配置私家车资源,提供用户有限的使用权。“人民”的实际所指是自由市场上的消费者和私家车租赁者,“人民优步”似乎也给网约车抹上了天然的道德正当性,暗示反对的声音是腐朽的、落后的、糟糕的“敌人”。与此同时,优步在西方国家进行媒体公关的话语策略却是巧妙挪用“民主”一词,将消费者与政治选举的投票人悄然划上等号。而这两种话语都意味着将企业等同于社会,无论是“人民”还是“公民”。反对新经济,就是反对社会,就是与“人民”/“公民”为敌。
祛魅“国民素质论”:不配合新经济就=不具备现代公民的基本文明素养?
信息革命往往被定义为提高人类智力水平、改善日常社会生活、拓展人类对现实世界的掌控能力等等光明前景,技术的黑暗面和消极影响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共享经济”所仰仗的一套意识形态是,信息技术是进步的社会力量,而一切对于技术的拒绝和惶恐都是落后、愚昧和不识时务。国民素质论的甚嚣尘上则延续这一线性技术进步论的逻辑:反对或者不配合新经济就是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不具备现代公民的基本文明素养,是粗鄙、低素质、不配使用新科技的“游民”,甚至将这些社会现象上纲上线到对中国人整体素质的批评。一方面,将反对者开除出现代社会生活的公民群体,另一方面则暗示技术推动者(互联网企业)是复兴公共生活的希望。舆论一边嘲笑“低素质”人群拒绝适应和使用新技术是多么可鄙和迂腐,一边暗示新经济能够让我们回到田园牧歌式的理性公共生活。
可是公共生活何曾是建立在市场之上?即使在欧美语境里,国家、市场和社会也是互相独立的三角关系,社会与政府和市场两者截然区分,市场从来不意味着公共性,相反公共领域要时刻警惕市场对其的侵蚀。在国民素质论的讨论浪潮中,曾经作为政治概念的“人民”被挪用为网约车的商业模式摇旗呐喊,公共性也被偷换概念和简化为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个人素质和社会信用问题,并且部分人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竟然只是将用户而不包括这些信息权力过于庞大的公司列为监管对象。企业对个人资料和使用行为的搜集、记录、分析和利用的权力边界有谁来制约?究竟谁才是破坏线下公共生活的主角?谁才应该接受公众的监督呢?
我们对于新媒体技术的认识仍然沉浸在浪漫迷思中:科技是解围之神,它将改变一切,且将顺着好的方向发展,只要我们听从它的召唤。这套论述的主要观点包括:技术必然是有益的;技术是中立的,它本身不具有价值取向,关键在于人们如何利用它;技术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而很多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将信息革命仅仅作为纯粹的技术创新来理解非常幼稚,它们实则抑制和遮蔽了存在于信息技术运作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和结构性的政治经济力量。要理解信息技术的社会影响,必须考察信息技术与资本市场、国家政经制度、产业所有制结构、代码空间的权力架构之间的关联。对于欢呼信息革命的技术乐观派而言,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市场机遇和新技术带来的商业潜力。对于他们而言,要的不是公共性,而是以公共性为名号召大家为新经济免费打工且乐此不疲。而新卢德主义者对此的回答是拒绝。(文/章玉萍)

手机浏览,点击图片保存二维码到相册,然后打开微信扫一扫选择本二维码图片就可以进入,电脑端微信“扫一扫”二维码,进入找聊天搭子平台,里面有找饭搭子、找对象、找陪伴服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