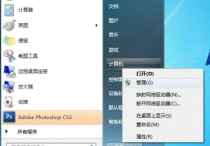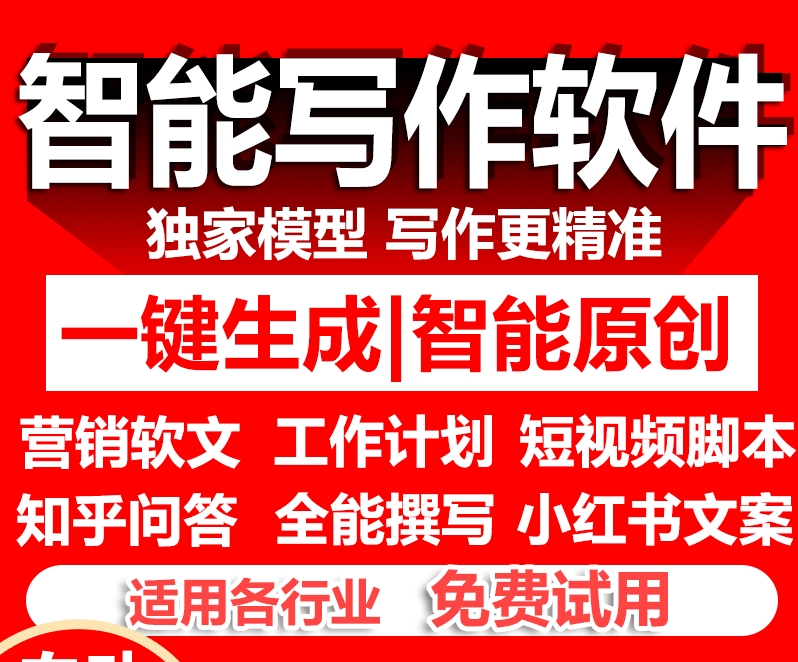中国城市土地公有制的优越性与相对性
在世界上实施土地国有化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许多西方国家近年来都加大了土地国有化力度。但这都不能说明中国既有土地公有制的高明,更不应当成为否定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依据。因为,多少年来人家始终存在着健全的土地市场,而中国的土地国有化却是以消灭一切土地市场、排斥所有土地交易来实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指导土地公有制的理论进行认真的剖析。
由于旧中国的土地私有制黑暗得不堪回首,那么在新中国实行无市场交易的土地公有制,从理论上看绝对是一个让亿万国人激动不已的理想,在土地资源存量、技术利用能力和人口增长趋势等因素不变的假设下,土地国有化至少可以体现出社会意识、公共选择和收入分配等重要方面的优越性:
一是人人在意识上自觉拥护和执行土地公有制,社会生产要素的任何所有者(试想共享经济与公有制的关系共享经济与公有制的关系,某“劳动模范”本人即使不拥有土地,却可能怀揣着使土地增值的特殊技能,这一生产技能常常与本人自身牢不可破而与社会分离)之间的思想,不需要任何“激励成本”就能达成心照不宣的、完备的献身公有制的“契约”。这意味着社会意识和教育的“零成本”。
二是各社会组织、包括政府(如果还需要它们的话)均没有自身利益目标,公共选择的偏好都是国有土地产值的最大化、结构的最优化。它们能够精确地在任何条件下(包括实践中一定会出现的意外情况)严格遵守土地公有制契约,自律大大降低了“社会监督成本”,这意味着公共协调和管理的“零成本”。
三是齐心协力的人们不仅找到了最佳的社会土地资源配置格局(它的存在是变化的,以现有知识和智慧来寻找最佳配置真是麻烦多多),而且其高收益在全社会绝对公平地分配着,充分满足的“消费列车”只会向更加美好的方向前进……人们也不会再有享受上的边际效应,因为生活将日新月异。这意味着社会分配和积累的“零成本”。
我们还能继续对“零成本”或低成本的土地资源公有制构想下去,直到思索的边际。但计划经济时代的土地公有制理论假说,却是建立在相当苛刻的社会条件上:其中,人的意识、公共选择、社会运行成本等实际变量,都被设定为合理的、可知的、不会变坏的、或一定能通过努力变好的固化参数,这样宏观上的经济计划才比较容易制定出来。
然而,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理论上的重大进步正是实事求是地承认:公有制在中国决不会无成本地变为社会实现,新中国建立以来从不曾具备过这样高难度、高成本的社会客观存在。经济的人和独立的人恰恰为国家制度规范奠定了最客观、最现实的基础。
今天改革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分析社会意识形态与土地公有制的关系。新中国实行土地公有制之后,虽然得到了全社会90%以上人口的衷心拥护。但国家并没有以相适应的机制来引导和激励这一可贵的社会思潮,而是过高地估价了当初的“高比率拥护”,甚至认为社会的普遍觉悟已经到达了“无需交易成本”式的公有制水平,这是新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缺憾。
以后多年,即使经过“大跃进”、“学雷锋”、“文化大革命”等共产主义式的政治运动,广大市民们对土地国有制的认识也大多局限于“欢迎无地租剥削时代”的到来。这不仅缺乏对新的“国家地租”和“利润计提”的深刻理解,而且与理论所构思的无市场的土地公用制应备的崇高社会意识也无法相提并论。总之,当年高比率“社会拥护”的性质,与其说是人民为新的土地公有制欢呼,倒不如说是为旧的私有剥削制度送终。
当然,土地公有制也曾为战后千疮百孔的中国城市经济带来过盎然生机,但1950-60年代中国经济的恢复不能完全证明土地公有制的合理性,因为制度的重新安排对国民收入分配和产出均有积极的影响,经济恢复和发展是多个变量共同运行的结果。特别是领导层如果忽视新产权对财富分配所产生的社会激励效应和边际时效,就容易大公有制的合理性,简单地认为国家经济一旦恢复就能自动、稳定地增长下去,以至不能理解国家土地公有制面对着复杂的社会意识和利益格局的双重“阻力”。多年来土地公有制所产出的资源低效、浪费等教训无情地指出:市场搞不好的事情,政府也不一定管得好!这就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勇气所在。
其实,不论人们怎样宣扬公有制的优越,理论研究只承认:制度对于土地来说总是相对的。一是因为地权是从土地资产中抽象出来的,绝对的无地产则常常意味着无地权;二是绝对的土地资产可以产生出多元化的相对的地权为人们的多种社会需求服务;三是地权与社会和意识互动多变,而土地资产则要稳定的多,土地作为全体国民的自然资源一般很少受人为的因素而改变其自我运行规律。当人们认为一切产权既定、完美到只需全社会努力前进时,却总是发现制度模式出现了危机。
权益和制度的相对性斩钉截铁地告诫人们: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地权和土地所有制。德姆塞茨曾深刻地指出:“新技术的发展和新市场的开发,都会促使旧产权发生不适而改变”(德姆塞茨,“产权导论”,《美国经济评论》,1967年5月第350页)。公有制的相对性正是我们改革合理性的逻辑起点。在土地所有制这样的开放系统面前,人们本来就拥有更多、更好的选择,没有什么制度是绝对不可以变更的。在多元化的发展与选择中,我们应具备先贤之勇敢和智慧,应比他们当年的选择更实际、更开明。
土地所有制规范的土地产权主要包括3方面的内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人张五常总结的:
一是土地的使用权:即在法律规范下自由使用土地资源的权利;
二是土地的收益权:即在法律(有时需要道德相助)的规范下收享土地资源所生利益的权利;

三是土地的让渡权:即在法律规范下出售、转让土地资源的权利;
当然,这“三权鼎立”之下人们还根据社会的多种需要,进一步细分出土地的空间权(对地上地下的占有程度)、地役权(设定相邻土地关系)、抵押权(以地设债)、他物权(让他人利用吾地)、国际地权(充许他国用地的限制)等等。但从现有的分析归纳中可以看出,细分之权还没有超出3个主要方面的内容。
既然土地产权是由一系列相关权利组成的、可分解的“权利束”,那么国家土地所有权的权威性也就不会总是绝对的了,而是与其组合权利的实际构成相辅相成。从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上看,其权力结构的分解过程仍将继续下去。而从理论探讨中我们也认识到,国家土地所有权的各项权能是可以、也应该在为了满足特定社会需求时,与所有权适当分离,这在适当的制度保护下一般不会影响国家所有权的地位,甚至是充分行使所有权最合理、最有效选择。
但是,“权利束”的分解只能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并且够能最终回归国家的。否则,制度上的漏洞也会引出“反客为主”动摇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因此,任何土地所有制一定要针对“权利束”的实际特点来进行具体的规范,这才是避免国家制度缺憾的关键所在,制度改革也正是应当在这些方面展开,而不能一味地讲国家制度不可变更。
再谈谈土地所有制性质上的相对性。从严格的概念分析中,我们也只承认土地的公有制或私有制都是相对的“模糊概念”,与长、短、高、低一样,说穿了只是在相对意义上对事物进行了定性。因此,法律上使用“国有制”在概念上显然更加清晰、准确。公有制与私有制在定性上又是相互依存的(无私即无公),所谓的“公有”、“私有”只是对实际土地产权拥有者的数量和排他范围而言的。
例如,中国城市的土地被法定为归国家所有,与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相比,当然无愧是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称谓,而农村的土地只归当地的那些农民所有,其中体现出“小公”或“大私”的含义。但是,如果同时把中国国土的所有制放大到全球范围去定性,那就堪称是“私有”的,绝对具有对全世界各国的排他性。因此,土地所有制的排他范围是确定其性质的主要标准。
从哲学思辩的角度来分析,土地的公有制或私有制本来就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只要社会主客观条件都具备了,公有制与私有制或巨变、或渐变,都可能最终走入相对的阵营去。这又多了一个动态中的相对性。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土地所有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从私有到公有的巨变形式。而研究此后国家所有制演化的实际趋势,则对今后土地制度改革实践具有深远的理论指导意义。
中国的城市土地确立国家所有制后,是以行政划拨方式,按计划供给各机构和单位无偿使用的。这是颇有“中国特色”的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从无偿性来分析,行政划拨所得的城市土地使用权,尽管有“成本”但决不属于转让,而更象是一种借用;但从对借用权的限制来分析,它又是无期限、不可流通的权利,至少在理论上与共和国同在,也就不是一般意义的借用了。这种定性上的困惑,恰恰为我们的土地公有制研究增加了浓厚的趣味。
其实,行政划拨城市土地使用权是公有制基本理论的产物,是更大范围内生产要素公有制的组成部分,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必然选择。由于消灭了市场,中国只能以行政手段来划拨城市土地使用权。而且,土地是国家的,用地单位也是国家的,国家的地租可以通过用地单位产出的统一归属来实现。这并不是一般西方式国有土地与用地者之间的转让或交易,而是一种特大型经济组织内部的公共资源配置。
为什么在全球经济市场化的时代,中国却要使用价格机制的替代物──计划供给机制呢?除历史演进因素外,从公有制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均可以得出近似的结论:即以行政指令来配置土地资源比引入市场机制更节约“交易成本”。因为,市场调协机制是建立在几乎各个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公开竞争、谈判、妥协和签约的基础上,其善后构建“成本”是相当高昂的,以至许多经济落后的国家难以在短时间建立起这样的经济机制。这里不仅指市场建设成本,还包括资源存量、历史延革和人文传统等成本。
在经济组织内部对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源)进行配置和安排则要简单得多,由于要素所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早在“参加组织”时就预定好了,服从组织权威和行政指令是公有制组织最基本的“契约”,对此来不得一点市场式的讨价还价。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协同运行中即使出现某些大的变化,从理论上讲也不会发生所有权性质变更的风险。对经济组织的所有者来说,这自然要比依靠市场调节、所有权随时可能异位的成本低许多。同时,这种土地资源配置机制也比市场协调更容易被组织权威所控制,更容易充分利用国家机器的职能,这多少超出了纯经济的“成本”分析。
中国在30年的计划经济时代里,几乎把全国办成了一个“超级航空母舰型”的经济组织,从运行成本上分析,其实施生产要素公有制所具备的对外竞争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如对国有外贸易企业和国家银行的“长青不死”。但是,为什么大一统的土地公有制优势没有最终形成“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生产效率呢?这恰巧是制度“成本”的另一辩证法则。
用经济组织的内部协同来替代市场交易、对抗成本矛盾等,也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其节约成本的效用并不是绝对的、无限度的,中国的土地公有制在节约交易成本时,也不可避免的丧失了相当多的社会激励,当社会意识、法规监管、资源供给等方面出现差距时,经济组织规模的无限扩大就带来与理论初始设计相悖的结果。可见,土地公有制的初始“成本”又是一个相对变量,并不足以代表理论体制的“全能”。
事实上,在任何经济组织的实际运行中内耗是不可避免的,组织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内部成本的同步上升。当组织内部的成本和矛盾大于市场交易成本和矛盾时,经济组织就达到了规模效应的极限,再前进一步就意味着对初始成本优势的反蚀,土地公有制的“负效益危机”正是这样发生的。其实,关于经济组织过于庞大的风险,并不仅限于中国的公有制经济,类似的问题在西方世界也比比皆是。美国学者阿尔温.托夫勒在其名著《第三次浪潮》中详尽地描绘了西方“大公司的共同危机”(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4年,第313页)。这就明确地告诫人们:任何比较研究首先必须是动态的比较。
行文至此又不禁想到,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不也是在反复强调:“我们必须考虑各种社会格局的运行成本(不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管理体制)和转成一种新制度的成本。在设计和选择社会格局时,我们应当考虑总的结果。”(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第124页。)可见,对既有国家土地制度的重新设计肯定是中国一切改革者最正当、最合理的选择。

手机浏览,点击图片保存二维码到相册,然后打开微信扫一扫选择本二维码图片就可以进入,电脑端微信“扫一扫”二维码,进入找聊天搭子平台,里面有找饭搭子、找对象、找陪伴服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