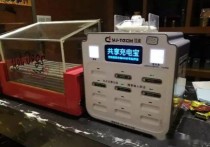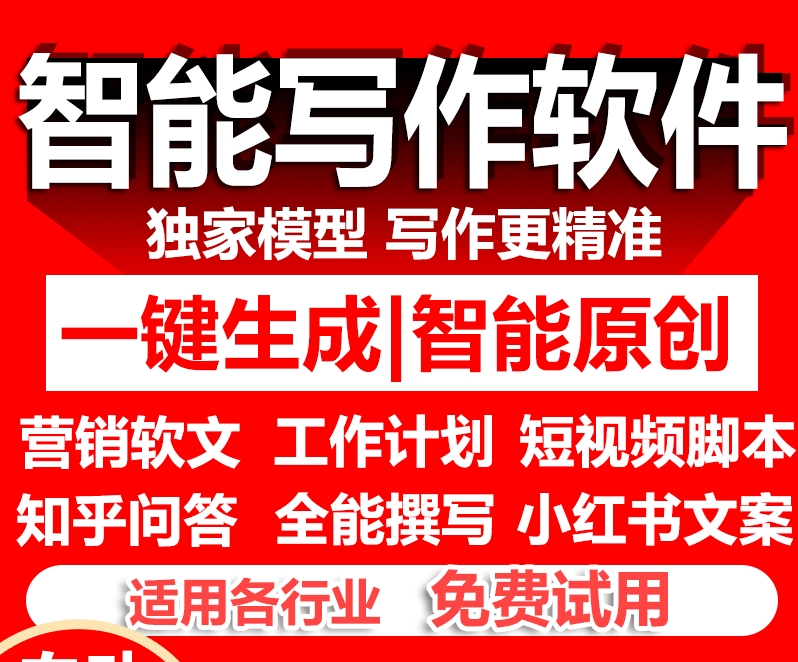面对“共享经济”的种种问题,人们开始尝试“平台合作主义”

“共享经济”在诞生之初就被各种浪漫的、进步的光环笼罩着,比如,共享经济给就业带来灵活和自由,让闲置资源得到利用,对环境好,减少中介,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废墟给普通人一条就业出路,甚至可以为孤独的人创造社交机会……其中一些确实没错,但只是对有些人,在有些时候。
对它的批评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比如 Uber、Lyft 等事实上将其平台上的劳动者(司机、保姆等)作为企业核心劳动力的公司,却将这些他们视作“独立承包商”而非雇员,因此可以不必他们提供社会福利和最低工资保障,而这些劳动者也失去任何组成工会与事实上的雇主谈判的能力。结果是社会上出现了很多以零工(或多份零工)作为全职工作的不稳定就业者,其中很多人收入微薄甚至负债累累。这与共享经济企业所描绘的“分享”闲暇时间和资源的赚外快者的身份十分不同。而与此同时,它们给与之形成竞争关系的传统行业(比如巡游出租车)造成巨大的冲击。

2015 年 1 月美国波特兰的一场抗议,460 辆巡游出租车的司机要求网约车遵守与出租车同样的规则,图片来自 Flickr 用户 Aaron Parecki
Airbnb 则把具有全球支付能力的游客大量输送到旅游目的地,彻底改变了一地的住宅租赁市场,创造出一种新的“士绅化”现象,让低收入者、年轻人租不起房。
这些以分享为口号的公司最后成为一条价值链上唯一的中介,向它所连接的两头同时收费,用巨额投资铸就的垄断地位让它们享有强大的定价权,让他们的生意本质上成为一种收租行为。而这些并不投入一辆车、一套房,不维持庞大员工队伍的 APP,却因此在极短时间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运输和旅馆企业,有着天文数字的估值。巨大的经济实力让它们甚至有能力影响政策,对抗监管。
正是因为同时看到“共享经济”的这些问题,以及它通过互联网连接数量庞大的个体、开展 P2P 合作和交易的潜力,一些人差不多在共享经济兴起之初的 2014 年就开始谈论一种新的模式——“平台合作社”(platform cooperative),它试图把有着漫长历史的合作社传统搬上 P2P 互联网的“平台”。他们把这种思想称作“平台合作主义”,而所谓“共享经济”在他们看来本质上是“平台资本主义”。

“平台合作主义”一词的创造者,纽约新校大学教授 Trebor Scholz,图片来自 Flickr 用户 Rosa Luxemburg-Stiftung
合作社不是共产主义国家的特产,也不是农民的专利。现代合作社运动的一个重要源头是 1844 年在英国成立的“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这是一个消费合作社。起初 30 名工人每人拿出 1 英镑,投资开设一家小店,销售生活必需品。借助抱团采购、共同投劳,以及小店利润在社员之间分享,这些贫穷的社员们可以买得起他们原本买不起的必需品。此外他们还把商店的利润投资于其他一些向社员提供社会保护的事业。这种为会员共同所有,会员具有一人一票的民主控制权,按照贡献(劳动贡献或者消费贡献)分配剩余的模式,成为后来所有合作社的基本原则。
这与由股东控制,根据股份多寡分配剩余,员工只领薪而不参与决策的商业公司模式十分不同。它的核心价值不是个人财富冒险和财富积累,而是一个群体通过互惠合作来实现共同的福祉。
2014 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DESA)做了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合作社普查。发现当时全球合作社拥有 20 万亿美元资产,年收入 3 万亿美元,经济总体规模仅次于德国,大于法国,如果是个国家共享经济-必信力,可以排名世界第五。全世界有 1260 万员工在 77 万个合作社中就业(不包括中国的 98 万多个“农民合作社”)。一些合作社可以十分巨大,比如印度最大的食品品牌 Amul 是一个奶农合作社,在美国有 154 家门店的户外运动装备品牌 REI 是一个消费者合作社共享经济-必信力,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 Mondragon 集团是一个年收入达到百亿欧元、雇佣七万多人的工人合作社。
事实上,已经有了很多“平台合作社” APP。比如 La`Zooz 是一个去中心化、社群共有、使用加密货币的拼车服务;创办于美国旧金山的 Loconomics(名字意指“本地经济”)则是一个对接本地服务需求和供给的 APP,它上面所有的服务提供者都被称作“所有者”(owner),可以选举合作社理事会,合作社产生的盈余根据“所有者”的贡献进行分配,真正取消了掮客,哪怕是共享经济掮客,实现利益共享。
平台合作社不仅仅是合作社版的“共享经济”,更是合作社版互联网经济。就像合作社涉足传统商业的各个领域,平台合作主义也可以用来实现传统的互联网商业。比如创始于德国的 Fairmondo(名字的意指“公平世界”)就是一个合作社版的 Amazon 或 eBay。
这样的实例还有非常多,涉及大量行业,本质上它们不是要取代“共享经济”,而是实现一种开放、民主、去中心化、为大众共有和共享的互联网,并用它改变经济生活。因此,它就像是合作社运动和 IT 界的开源运动(open source movement)的结合。

两位平台合作主义倡导者 Trebor Scholz 和 Nathan Schneider 关于平台合作主义的著作《我们来编程并拥有》,图片来自出版商 OR Books
作为一场正在成长中的全球性运动,平台合作主义已经有了著作,信息和倡导平台,以及国际会议。
平台合作主义联盟(Platform Cooperativism Consortium)从 2015 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国际大会,在今年 9 月 28、29 日将举行第四届,名为“播种:亚洲的平台合作运动”,据说是平台合作主义在亚洲的首场国际性交流,地点在香港中文大学。在会议之前的两天,还安排了一场名为“合作松”的开发竞赛,这个古怪名字来自于“合作社”+“黑客松”,后者是一种流行于技术圈的“编程马拉松”活动。届时,来自两岸三地的 IT 技术人员、合作社人士、艺术家将在一起开发平台合作主义项目原型,比如网站、APP、数据库,甚至是游戏。
这或许会给崇尚共享的我们带来更好的选择,并让“共享”的含义变得更加丰富。
题图来自 Flickr 用户 Kamil Kubaczka


手机浏览,点击图片保存二维码到相册,然后打开微信扫一扫选择本二维码图片就可以进入,电脑端微信“扫一扫”二维码,进入找聊天搭子平台,里面有找饭搭子、找对象、找陪伴服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