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剩的共享单车”占据了街道并需要专人去“运输”
图片:空空
潘赫认为出租车因其行业垄断性或许不是一个讨论共享经济的好例子。在他看来,真正的分享经济不仅分享使用权,还分享所有权;而分享所有权经济导致的问题引发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难题。同时他也质疑王洪喆关于希望借由政府大力监管来有效建设共享经济,提出还是要依靠公众自己建立平台,并且在建立之初就实现平台制度透明化。
王洪喆通过对大陆出租车历史简要梳理,指出被忽略的作为公共资源的道路使用问题。随后又谈到政府管理职能的退化导致出租行业垄断性经营。举出几个城市的例子希望打开更多共享经济的选项。在谈及研究初衷时,王洪喆明确希望借由对互联网经济的批判,探索建立新的共享经济模式。现场讨论谈及何为“真正的共享经济”,也就是平台共享主义的话题。
宋轶直接指出潘赫谈到的以共享单车为例作为“撬动”城市规划的支点的现实复杂性。一位观众则把问题从宏远处拉近讨论近期内共享单车给城市带来的正负外部性。另一位观众对五年内的共享单车发展趋势表示兴趣。其他观众把问题指向公共服务型产品设计。
以下是都市折叠展览系列活动《什么是共享经济?(下篇)》的详细对话。
对话嘉宾: 张涵露王洪喆潘赫宋轶王易郑源观众
潘赫:关于 “罢工”需要区别两个概念,出租车车主和出租车司机。一个城市在滴滴或者优步进驻之前,车标的拍卖价钱可以是100万。很早的时候是政府垄断,一次性拍给所有出租车公司。随后车标可能降价为80万,甚至降到30万。这种情况下,出租车公司一定会维权,但这种维权是不是正义?
第二点是我认为出租车可能不适用于讨论共享经济。在中国出租车是一个非常垄断的行业。这是一种垄断的管理方式,由交通局卖车标给出租车公司,到出租车主,然后再到夜班司机。与出租车的管理模式相比,滴滴对于个体的剥削稍微少一点,它可能产生利益。另一点是在中国我们是不是要支持一种行会主义,这是行会主义还是一种共享主义?比如说新华社,官方支持共享经济或许是因为它把所有的司机都变成一个原子人,这令统治变得更容易。而在回顾当年的欧洲在形成近代社会的时候,行会也确实拥有垄断利益。一个个垄断的行会通过内部的民主化慢慢相互聚合,而形成今天的民主社会。美国则是一个巨大的国家通过一种天赋人权而形成民主社会。对中国来说,出租车司机这个行会是一个小团体特殊的利益,对国家整体利益造成威胁。在一个普遍正义的情况下,出租车行会建立在一个非常垄断利益的基础上,是非正义的。所以它不是一个讨论共享经济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假设说有闲置资源的人把以此为生的人挤出市场,这违反了职业主义或者行会主义的原则。这种资源配置实际上是一种共产主义的先声,实际在真正的共产主义是不是我们不应该有行会和职业利益,而是所有人都是通过自己配置闲置某部分才华、资源而形成相互之间的共享。
王洪喆:我和你观点类似。昌平拼车群的例子是一个理想模式。但目前这种共享经济也是一种互联网的垄断经济,以金融资本来驱动,本质上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特征。投资人或风投把这些钱投给滴滴之后,一定要能见到回报,因此推动公司以谋利作为主要目标,从而涉及到一个平台的公益性的问题。我对共享经济是绝对支持,但是对如何发展共享经济存有疑问。除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大公司模式,还有没有另一种平台合作的模式。比如中国这样的国家,国家依然强大共享经济的垄断效应,在很多方面行使公共管理职能。有没有可能促成一个比现在来说不那么邪恶,或者更有效的一种方式?回到出租车垄断利益形成的历史波折,我一直在思考是什么使垄断变成双方争夺的事情。在此作一点历史梳理来说明其复杂性。出租车这个行业的兴起大概是在80年代末期的北京和上海出现小规模国营公司。当时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则是小轿车不应该是一个主要出行方式。到了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政府开始鼓励私人来运营。那个时候不但没有份子钱甚至还补贴。只要你愿意当出租车司机,政府就给你补贴;牌照也是一经申请就颁发。大概1992至1995年都是这样,然后到了1995年那个时候,市场绝对自由后,秩序就失去控制。路上的面的横向乱跑。
那个时候李春波有首歌叫作《广东为什么那么堵》。也就是那个时候才认识到道路是一个公共资源,在道路上各种出行方式是相互排斥的,小轿车的数量必须有一个限制。这个也是道路资源比较紧张的国家的惯常的做法,比如日本、韩国和香港。尤其是香港到现在也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共享专车,并且执法力度非常大。那时,国家的应对策略是出台了一个牌照政策,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1995年时的管理力度比较大,当时中央有一个叫作交通运输委员会来负责牌照的审批和管理,而且那个时候牌照是既可以审批给个人,又可以审批给公司,个人和公司之间没有歧视。但是后来这个管理的职能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到了地方很多政府追求经济繁荣的方式是倾向于把牌照租赁给公司,公司会给它一些返还的利益和好处,因此变成利益输送关系。原本的政府管理职能消失殆尽。我认为正是这种管理职能的倒退导致市场变得垄断和封闭。相反,当你观察管理水平较高的城市,比如直接把牌照发给个人的温州政府和采用国营模式的上海,会发现这两种模式导致的现象非常不一样。滴滴进驻温州,出租车司机的抗争就非常剧烈。因为这些牌照是归个人,他们还雇了跑夜班的人。类似的还有天津,打车非常慢。天津的牌照也是归个人,因此没有公司份子钱的限制,所以司机们每天开三个小时,把钱赚够就回去,不愿意多拉客人。在这样的城市,专车和传统出租车之间的矛盾非常剧烈。上海却恰恰相反。直到今天上海主要的出租车公司还是国营的供应厂,所以反而这个矛盾在上海没有那么厉害。政府不仅对国营的出租车管得严,对滴滴平台管得也严。监管力度很大,不允许高额份子钱,或者任意把这个车包给别人或雇人开。这样反而导致市场更加公平,我在这一系列操作里看到问题的复杂性。
潘赫:但这只限于政府管理比较好的地方。像是东北的地方政府只想着赚钱,把自己当成谋利的集团,任何东西只要是公家,都会做的很差。
王洪喆:我也是这么认为。
潘赫:例如2003年沈阳市经济最差的时候,把所有出租车车标一次性从政府卖给出租车汽车公司,并且签订协议承诺永远不加出租车车标。过了这么多年,出租车的数量早已不能满足需求。即便是签了一份非法的合同,政府也不能不遵守,这成了一个困局。沈阳绝大多数的中年人不会用滴滴,打车还是传统方式,所以出租车司机还是大爷。比如说打出租车时,一进去发现司机在吸烟,然后我请他不吸烟,司机会直接拒载。每天都跟出租车汽车司机有非常强烈的冲突。前一段的新闻报道,沈阳桃仙机场离市区只有18公里,但是出租车司机对外地人一般要价180元。司机绕着整个城市的二环先转了一圈再给进市内。这时就产生了政府监管的死角,只有在优步最开始进驻且还没有被滴滴收购的时候,出租车司机才有所收敛。
张涵露:刚刚潘赫提到的是真正的分享经济,我想可以详细展开你认为什么是真正的分享经济吗?
潘赫:真正的分享经济不仅分享使用权,还分享所有权。但分享所有权的经济会产生问题。例如大家共同组成一个商品生产为主的公司,所有人出资相同,没有多少之分。这就好比在社会主义情况下,到最后考虑盈利时,作为竞争主体和别的国家相比资本太少。这也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很难的原因。在作为国际竞争主体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就变成大家的利润都被压榨到中间作为一个所谓的共同利润。这个东西用来再投资,但这个再投资的必要性质因为它处于资本主义的环境下。
宋轶:刚才王洪喆提到的昌平私家拼车群,看起来是一个更好的模式。私家车主在这个群里其实是不盈利的。但是这个群的自然解体来自于利益诱惑,或者是一种经济的竞争。不管是滴滴还是共享单车,其实更像互联网创业。只是说在互联网企业创业过程中,如何跟官方作同样事情,所谓企业去竞争。我认为我们其实更多是讨论这个问题,而不是共享经济这个词语带给来的内容期许。其实还是想回到你在研究之初和过程中,你觉得有什么期待或者过程中有发现什么,让你仍然觉得这个研究有意思。
王洪喆:我的期待主要是批判这些互联网企业,因为赞美他们的话太多了,不缺我一个。我研究的是互联网经济,包括新媒体这套历史。它们的确创造了很多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动员了人们对一种更理想社会的一些想象和期待,变成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这种想象和期待普遍存在我们的每个人日常生活和愿望当中。但是用一个不恰当的说法,当这些想象和期待变成一个互联网融资创业项目时,就把这种期待和未来的可能性给垄断了。我在想有没有另一种可能性,比如说把平台公众化,不允许任何人在这里挣钱,运营是纯粹分享式的。把闲置资源分享出来,产生一个物物交换的模式,但凡任何人想在里面获益就被踢出局。是否需要有一些比较严格的界定和规制,共享经济才能运行。因其本质上无法跟盈利的经济去竞争。例如Airbnb,也会有大酒店把整栋公寓都租下来以成本很低的方式去经营,因为低廉的价位把私人经营者排挤出局。
宋轶:但是这样也会进入到潘赫刚才说到的那种循环。即便滴滴的平台公共化,但仍然在面临一个外部要求利润或者要求竞争的经济压力。
潘赫:或许应对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从很少的人开始,自己建立和共享这个平台。在平台最初建立的时候,所有的算法和程序都是开列的,连数据的买卖都需要透明化。对于监管者,永远只能想到最简单粗暴的方式不会具有先进性。相较于共享专车,共享单车是另一种共享经济的讨论。如果开车的人居多,大商场由于停车便利更受青睐,小商业模式受到打击。我会想到共享单车的外部效应。有一些想追求小商业模式的资金风投,他们提倡这种生活方式,而作为平台自身不盈利。共享单车不不直接盈利,而是通过一种铺开的方式,对于这种生活方式本身附加其他的经济活力。这可以说是一种资本主义。中国的许多新城已经变成了汽车城。汽车城在共享单车的冲击下,人们会不会重拾老城思维?
宋轶:感觉你说的太理想化。我明白你刚才说的意思,因为步行方式和交通工具使用习惯的改变,可能反过来刺激城市设计、规划到生活方式的改变。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触及的面太多,所以很难达到你所说的那种效果。目前而言,我觉得共享单车就是提供给用车人以灵活性和便利性。要想达到你说的那个层面我,我认为还需要有更全面和系统的构建以及政策的扶植才有可能。
潘赫:不同的城市规划差别很大。沈阳的路面非常差,人几乎没法骑车。在这种情况下,共享单车实际上变成某种当代生活方式的加权,把之前的城市短版全都暴露出来,这样会造成你在每个城市之间生活的感性差异增大。在实事求是上加大了人感性的不平等。但我并不认为我们要因此反对共享单车,而不是因为不平衡,所有的人都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但不可否认,监管回到原来的方式会更容易。
宋轶:当然可能用一个支点翘起一个地球。但是现实操作中,一方面取决于城市本来的管理或者监管者,另一方面取决于这个支点。比如共享单车这么一个主动方式推行者,是否能够成为撬动城市改变的支点。
潘赫:这恐怕还需要一些复杂的设计,因为本地的公司没有办法跟政府的垄断利益竞争。我是说像东北这些城市,政府就是垄断利益集团,把城市的所有行业都给垄断利益化。大多生活其中的市民感觉不好,这时候是否需要一些外来的工序来突破,在政府眼皮底下看不见的地方进行某种改变,使公平化变高。其中矛盾深刻。
张涵露:我非常好奇共享单车有没有对网约车的效益造成了影响?或者你觉得会不会造成一定影响?
王洪喆:共享单车的公司宣称,此前网约车力度比较大,短距离三公里以内的出行,乘客愿意选择打车。就我个人观察而言,现在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每个人标准可能不一样,如果10元对一个人来说是可接受的,他就选择坐车去接受一个更好的服务。省钱早已不是唯一的考量。但如果说滴滴价格变贵超出乘客接受范围,在此前提下他才会去选择骑车,而不是因为骑车可以锻炼身体。再者,一个人之前可能3公里内选择走路,但现在共享单车解锁特别方便,他自然认为花0.5-1元的价格,比之前快很多。本来一个习惯走路的人,开始习惯变成加速的一个人。这和网约车特别像,本来3公里之内习惯走到地铁站和商场,现在有一个特别便宜的车可以打,他可以加速。目前看来共享单车是增量需求,原先没有骑车需求的人现在需要加速。
张涵露:现在大街泛滥的小黄车已经远远超过我们需要的数量,我有天突然想到,如果车的数量大于我们需求的数量,那么共享的字面意思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共享单车其实是一种金融资本。
王洪喆:实际上共享单车的投资人就包括滴滴其他网约车这样的公司。
潘赫:我觉得共享单车对于一般人的感性改变是使一些人感觉到自己更像是城市的主人,或者对城市多了一些支配权。以此让市民觉得这个城市和人之间关系更近或城市真的使生活变得美好。要是有这样一种感性,人们可能会开始要求政府和企业共享出另一部分产品,或者真正在很多事物上要求共享。互联网五巨头很显然是垄断利益。比如每次使用谷歌时,我们都对平台输送了某些资本。在不付费的前提下,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要求都是不付费。包括我们在网上可以下载一些东西的时候,对于现实世界上某些东西的要求是不是也是免费?这样一种感性的循环可能会打破一些版权主义的东西。在现实世界里,这种版权主义跟原来一些垄断经济集团利益是一回事。
张涵露:这个前提是不是要调查一下大家对单车是一个功能性使用还是真的具有某种认同感。像我自己也是下了多个共享单车软件,是一个非常工具化的使用。要达到你说到的这个可能性,是不是需要在我们对这些平台的认同意识上做一些工作?
潘赫:比如在上海和深圳有很多公立图书馆供市民使用。在二三线城市,政府没有这种公共服务意识,也不希望培养这种意识,而希望所有项目都是收费。政府之所以不愿意提供各种公共的开口,或许是因为担心提供了一个后,市民在感性上要求另一个。但是共享单车可能就是这种东西。这在服务意识高的城市里,大家可能没有太过强烈的感受;但是对我来说就很明显。我竟然可以在城市里使用一样不是我所拥有的东西,并且只是需要象征性付费。
张涵露:这种象征性付费是短暂还是长期?会不会演变为网约车那样,一开始收费低廉,等大家形成了这个消费习惯后,开始涨价。
潘赫:二者不同,因为出租车还是一个刚性需求,但是自行车不是。自行车是增加了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有一天如果不划算,你会到原来的生活方式,它不会给你造成这样强迫性。
观众1:我想从价值观认同上和品牌上我跟你是一样,我觉得自行车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我会从社会的经济规律大概提三方面的想法,第一是对于城市规划上整体改善对大家生活的改善,我觉得这是一种理想,理论上可能实现。但是它毕竟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段,也就是说共享单车需要存活这么长一个时间段。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暂时搁置不去讨论它,因为有很多更加迫切的问题。出租车是一个垄断行业,政府形成一个垄断主体,但是在自行车这为什么没有成功。不仅在中国,包括在台湾都实行得不太乐观。共享单车是城市的单车,对市政府来说一直是一个开支而不是一个盈利点。政府为什么要去做这么一个东西?因为这其实是公共交通系统的一部分。需要把单车分开来看,它构成单车、地铁、包括出租车在内的整个交通系统,整个交通系统影响出行各种方式选择。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当资本介入,单车比出租车更接近公共财产。所谓公共财产我觉得就如同刚才所说共享经济的垄断效应,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割就是属于公共财产。公共财产天生有个问题,它有个负外部性,就是大家偏向于过度使用它,所以这些东西损坏非常快,而且使用权怎么分割,这是关于公共财产非常基本的一个问题。我对共享单车的了解还有待增多,但是我知道目前这几家共享单车都是没有找到盈利模式的。所以现在他们在做的事情和我们看到所有互联网创业企业一样,他们要先知道这个市场,然后进行垄断。所以在这个事情上,结合你刚才提到一点,投了共享单车是滴滴,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讲得更完善。
王洪喆:滴滴的高管已经空降ofo里面。
观众1:那我觉得共享单车下一步也是这个(滴滴的)形式。
宋轶:只是扩张到它的不同领域,从汽车到单车。
观众1:它实际是通过把控市场实现总体的盈利,不在乎小量市场。就是到时候无论是ABCDE哪一个选项,都是在他给你的蓝图里面。所以我对这事没这么看好。正如你刚才所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正外部性,确实带动了一些小商贩,比如你在骑车的过程中会停下来买水果。和负外部性相比,这个正外部性到底有多大?而它的负外部性超级大。街上全部都是单车。以前不骑单车的人现在骑了,人行道上到处都在逆行,乱七八糟。到处都是单车,这也是成本,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包括在现在在一些二线城市,大妈锁着单车不让用,产生各种各样社会性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它的负外部性都是所在。
潘赫:因为我不开私家车,我反对汽车这个东西。我们是否要在私家车车主这一面考虑共享单车给这个城市带来的负外部性,还是原来步行的人的角度?
观众1:应该是要从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在城市中生活的人。
潘赫:但是我会认为说私家车这种方式本身是一个不应该提倡的生活方式。
观众1: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一点:至少在北京,共享单车和私家车的用户问题。私家车通常是已经成家。在有私家车的情况有多少人去骑单车,我打个问号。但是骑单车更多都是更年轻的人。
潘赫:我比较兴奋的是共享单车的出现对这种城市的汽车主义来进行反扑,就是要扰乱这些开车人的方便。
宋轶:这个东西还要具到不同的城市和社会环境中,它可能起到的效果不一样。刚才这位朋友提到,不同的城市的负外部性成本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提到的一点是,这个东西出现以后,你能否找到一个更加适合它逆性生长的地方。
潘赫:他说的负外部性在我看来是正外部性,就是干扰私家车的出行,是让你开车的时候不感觉这么高兴和舒畅。
宋轶:私家车使用的理由也是不同的。在有些地方很有必要性,有一些地方没有那么有必要性。比如说南北的区别,这个城市的规划方式和所在的自然环境,北方特别到冬天的那种温度。
潘赫:这样的话,有一些人他在城市里开车没有感觉到那么爽,对我来说这件事很爽。为我反对那种规划方式,或者反对这种生活方式。像北方很多规划都是拍脑袋决定的。
宋轶:我觉得城市规划影响因素很多,有可能是资源、历史的因素,有可能很多别的,但是有一点要强调,当一个形式出现的时候,是否有可能去找到最有可能生长起来、给社会带来正的外部性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有意思的。
张涵露:那谁去找?
宋轶:所以说这个是合力。
王洪喆:我想到一个关于这种正外部性需要论证的观点。大家要形成这个认识,比如城市单车项目或者类似的公共交车地铁,不光是单车不盈利,大城市的地铁也需要政府补贴。为什么政府要补贴这个项目,是因为认识到政府交通设施会带来其他正外部。政府在这个方面补贴,会繁荣其他经济,或者在其他地方把这个钱赚过来,需要不同部门和经营主体之间形成这种共识。但是对于企业来说,确实比较困难,因为企业比较孤立。经营单车要赚钱,经营汽车要赚钱,经营别的也要赚钱。每一个板块都需要盈利。必须把这个利益整体的事业放在规划当中进行讨论,必须有一种公共能力的主体进行这个事业。
潘赫:所以我就在想在这个年代,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距离到底有多远?它可能组织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离得近。与原来的资本主义方式相比,两者是离的最近还是最远。有人说这是资本自身的共产主义化。垄断剥削的部分当成所谓社会主义实体交的税。
王易:资本就是要榨取剩余价值的,绝对比税收高。
潘赫:不一定,在中国我相信一定是反的。
王洪喆:有一种讨论说目前的互联网经济是靠投资驱动,这些投资之所以愿意进入这个行业,是因为有高额的利润,这个利润一定比所谓的社会主义税要高很多,这些资本才愿意进来。
潘赫:可以通过整体的平台加起来的提升来形成利润,剩余价值不是剥削到具体的人身上,这就是今天的资本主义。
王易:这个问题可以这么说,你刚刚说中国的税收高。那我们就把税收看成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那你是要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呢,还是要其他的某一种资本主义?
潘赫:我认为其他的资本主义好一些。中国的资本主义,军队就在那了,想管你要什么就要什么。是个人形成的资本主义好还是国家资本主义好?在面对国家资本主义时,个体无力抵抗,没有选择权。当枪口对着你时,你有什么选择权。况且它还有原子弹。
王易:但是他们都姓“资”
宋轶:这种个体的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变成一个如你所说的控制国家政权的暴力机器。你能保障别的国家不去效仿这种看着最好的方式?
潘赫:如果想要有军队,所费的力气比平台的提升要大的多。
王洪喆:所以最后变成一种讨论姓资还是姓社的一个问题。
张涵露:观众还有没有问题?
观众2:能不能你们分析下未来几年这几家共享单车的发展?你觉得ofo资金是从滴滴来的吗?未来5年之内哪家会退出市场?
王洪喆:是这样,据我有限的了解,ofo的思维是虽然它的车更容易丢失、损坏,但是成本更低。
观众2:对,我选ofo也是这个原因,像mobike要299的押金我就不愿意。
王洪喆:所以在目前两家竞争的情况下,看谁扩张市场更快。至于要预测,这个模式或者背后的计算是不是更理性,是ofo还是mobike的模式从长远看更加理性,我觉得不是我们所能讨论的。但是我看到一个具有参考性的说法。单车行业相对来说门槛较低,所以说在近期mobike和ofo看似垄断的程度,还有新的企业进驻。有人说现在赤橙黄绿青蓝紫所有颜色都已经用光了,新的公司没有颜色可用了,不是缺钱的问题。这也正是我认为有趣的地方。
观众3:刚开始有很多质疑公民道德素质的文章,对小黄车的损害。其实很反感媒体把公共服务设计问题导向公众素质,我认为这是设计上的失败。我感兴趣的就是这种公共服务型产品在设计的时候考虑的问题会比一般的产品更多吗?有没有公共服务型产品尽可能减少损害度?同时也有人讨论到,比如说ofo的损害度比mobike高很多,但是mobike比ofo要难骑很多,我觉得可能是轴转动的原因。我比较好奇的是有没有一款公共产品的设计是不考虑其他原因,它是一种尽可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所以既好用又没有那么容易有负外部性?貌似法国的公用单车也是不好用的。我对公共产品的设计方面感兴趣,到底哪些人在决策?然后什么样设计?怎么样去推出?
王洪喆:这个也是我想提示的跟设计比较相关的一点。互联网公司里面的产品设计不是以一个最好用,或者最合理、最优化来作为首要或者唯一的标准。他们也可能故意设计为不好来满足一些其他商业诉求。对于ofo来说这也是一种理性。想象一下,在损害的成本可以接受的前提下,设计得简单一点,让人们更容易打开,更容易解锁。这样比起竞争对手会有相对优势,市民会更多使用容易解锁的产品。可能有一些更合理的设计方案,但是在竞争时选择不拿出来。这都是有可能的。
潘赫:我是感觉到第一次骑到共享单车的时候,我很兴奋原因是这个车比之前打轮胎的自行车好骑。从第二代开始竟然可以不碰到打气、扎胎这些事情。以前可能是因为这些耗损,人们选择不骑自行车。我想是不是现在因为这些技术进步,所以又循环回来骑车。并且在循环回来的时候又升级了。
央美术馆(YANG ART MUSEUM,简称YAM)是一家将“现代性”与“美学生活方式”作为理念的美术馆,以亚洲为中心,举办包含世界各地艺术、设计等在内的当代艺术展览。同时也致力于公共教育项目和社区文化融合以及前沿性的文化探索,为艺术生活方式提供平台,促进艺术文化与城市生活的融合。
YAM位于北京蓝色港湾商圈,于2015年正式对公众开放,以社区、家庭为单位,以会员和社群为基础,拓展艺术外延,让文化良性介入公共空间,提升大众对艺术与文化的认知与参与。
YAM创立了“艺术生活工作坊“系列公共教育项目,吸引公众、家庭通过学习、交流、分享,一同拓宽视野,提升感受力,并培养艺术创造力;同时,YAM通过YAM Store,倡导有生活质量的精神美学,通过艺术衍生品及设计品,让艺术融入生活。
艺术、教育、商业与公共空间的有机结合,使得YAM在推动当代艺术传播与发声、学习与展示、跨文化与艺术门类之间的合作和知识生产方面,创造出全新的活力与吸引力,并以蓝色港湾商圈为核心,将该区域提升成为北京城市文化新地标。
按下方二维码,获取更多央美术馆信息
▽
地 址:北京市朝阳公园路6号蓝色港湾国际商区14号楼三层
开馆时间:周二至周日 10:00-18:00(周一闭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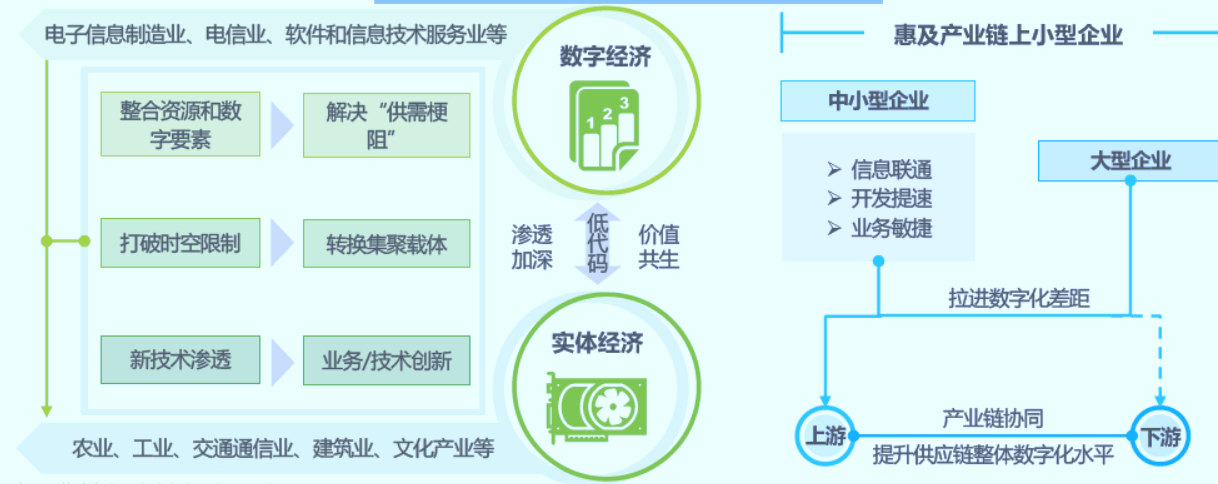












评论